叶林、雷俊华:“组织-空间”视角下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实现逻辑
作者:叶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增城区“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成员;雷俊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在传统的城市研究中,县及以下即属于“乡”的范畴,而在传统的乡村研究中,县级以上则属于“城”的范畴。因此,县城既可定义为“乡”又可定义为“城”,县域内既有城市的制度规范,又有农村的乡土特色,从而形成了我国城乡复杂的县域治理情境。随着我国传统“双轨政治”的分离格局,逐步转化为现代组织体系下的政治社会,县成为我国行政体制和城乡社会结构的重要层级。伴随我国城乡发展的不断演进,城乡治理的边界开始融合,城乡逐步成为一个统合的治理单元,县域则成为城乡治理单元的重要节点和城乡治理融合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县域发展的基础仍然较弱,城乡管理体制分割、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受阻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治理融合面临瓶颈。
一、城乡治理融合的现实要求、路径选择与实现梗阻
(一)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治理融合从历史来看,基于不同时期资源要素的配置差异,我国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阶段。为平衡城乡关系,我国城乡发展政策逐渐由城市偏向转向城乡融合的战略,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突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必须立足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并注重政府作用的发挥。实现城乡治理融合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而是需要依靠政府采取特定的制度安排,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各级政府如何通过帮扶协作组织在推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过程中激发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解决城乡空间的治理问题,实现城乡治理融合,成为重要的目标转向。
(二)城乡治理融合的路径选择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在当前市场制度不够完善、社会力量发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引导市场和社会的战略统筹作用尤为关键。随着县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帮扶协作组织如何在县域内推动组织协同联动和资源要素配置成为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关键。
从组织机制来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国在乡村振兴阶段延续城乡帮扶政策,向发展落后地区派驻帮扶干部(组织),从而由消灭“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如何在贫困治理的基础上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城乡治理融合路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主要任务。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涉及多层级政府的多个部门,部门和区域协作需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确保同向发力,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果。随着城乡帮扶从个体帮扶到区域帮扶协作,帮扶组织不仅要面临嵌入乡土社会的问题,还需要与基层政府开展协作,展开常态化互动,引导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实现城乡多元治理组织的协作。
从空间形态来看,我国正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县域成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解决城乡区域差距问题成为主要任务,需从空间尺度上考虑城乡区域协调问题。如何推动区域内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实现城乡治理融合成为新挑战。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重要空间尺度。实践中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尝试,如广东省的城乡帮扶协作政策就呈现出帮扶层级从个人到村到镇再到县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从脱贫攻坚时期的“驻村帮扶”(个人、村域)到乡村振兴要求下的“驻镇帮镇扶村”(镇域),再到城乡融合目标下“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县域)的演变。通过治理空间层级的提升,促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三)城乡治理融合的实现梗阻在城乡治理融合的现实需求下,我国提高城乡治理融合水平仍面临着梗阻,通过城乡帮扶协作实现组织管理体制的协同联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面临多元治理主体不协调、资源要素畅通流动存在阻碍等现实挑战。
组织管理体制协同联动面临梗阻。一是城乡组织协作的复杂性。在现阶段实行农村偏向和城乡融合政策时,不仅需要政府承担“兜底”职能,也必须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来引导市场和社会,解决城市资源要素下乡中的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二是城乡组织协作的多层级性。从个体帮扶变为城乡区域的帮扶协作,更强调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因此城乡空间内建立了多层级的组织关系。当前城乡空间内呈现出帮扶协作双方主体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增加了组织协作的复杂性。三是乡村治理转型愈发复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外流导致的农村原子化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发展悖论”,即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公共事务却呈现衰败景象。同时,与乡村“收缩性发展”一体两面的是城市的“扩张性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以城带乡”和“城乡互补”体制机制融合不力,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间难以实现治理机制的协同。因此,如何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构建统一的城乡治理组织框架,推动城乡共治,解决城乡组织管理体制协同联动面临的梗阻,是提高城乡治理融合水平的关键问题。
资源要素空间流动面临梗阻。一是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渠道不畅。由于我国农村发展历史负担较重,仅依靠农村自身难以突破发展困境。城镇化的进程推动乡村资源要素进入城市,但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则存在由于市场发育不足所导致的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缺乏成熟的市场机制支撑的现实障碍。二是城乡帮扶协作资源要素流动的单向性。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从个体农民及家庭的脱贫提升到城乡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仅依靠城市单向帮扶农村的方式难以保证农村区域的持续性发展,尤其是单纯的帮扶可能较多关注短期和形式效应,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性和内生性激励不足。三是县域内资源要素流动不畅。县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当前资源要素进入县域后面临县乡村各层级资源要素流动的梗阻,县域内的资源流动由于乡村治理纵向协调能力不足,可能产生“撒胡椒面”或“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组织-空间”理论框架
(一)城乡帮扶协作中的组织结构在传统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结构框架中,政府通过组建并下派帮扶协作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对市场和社会的引导,对接与当地各级政府的协作。一是政府赋予帮扶组织人员、资金、政策等要素以及对帮扶组织赋权。具体而言,通过设立激励制度和考核制度,能够发挥组织成员的能动性,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资源,推动资源要素下乡。帮扶组织可以利用其在城市获取的资源,推动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平等交换,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二是建立组织协调机制,解决资源下乡过程中经常存在的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现象。帮扶组织下乡能够起到统筹协调作用,引导市场和社会形成多元主体的合力。一方面,通过带动资本、社会等力量进入县域,提高县域内资源的增量,增强县域的经济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帮扶组织进入县域后,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推动城市资源与乡土社会相融合,发挥城市资源的带动作用,激活农村地区的发展要素,形成合力,推动县域发展。三是形成城乡科层组织的协作,引导县域各主体形成合力。帮扶组织进入县域后,由于其成员自身来自上级科层组织,能够与县域内各级科层组织形成互动与协作,提升县域内治理水平,进而实现城乡治理融合。
(二)县域城乡融合中的空间结构城乡融合的空间结构是基于城域和乡域的空间框架,县域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平台,是实现城乡融合的空间载体。以县域为核心,可以打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梗阻,优化城镇空间治理格局。其一,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环节,而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来看,县城则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天然载体。当前的乡村振兴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帮扶协作组织通过科学规划和资源整合,可打破县乡村之间的空间壁垒,构建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其二,县城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天然载体,具有空间上的制度优势。由于从城域到乡域资源要素链条较长,加之乡域基础薄弱难以直接承接城域的资源要素,将县城作为资源承接的节点,形成县域的城乡融合空间结构,可解决城域带动乡域缺乏空间支点的问题。城乡融合以县城为载体,能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县域为空间载体的城乡融合结构,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在县域内的融合。以县域为尺度的帮扶协作机制塑造的空间结构能够推动县乡村功能的协同互补。其三,县级政府组织部门齐全,作为混合科层组织的帮扶协作组织可以在县域内更好地对接业务部门,对全县发展政策进行统筹,实现各层级部门的科层协作和有效协调,形成良性的城乡治理空间,推动县乡村资源要素流动。帮扶协作组织通过构建多层级、多主体的科层治理结构,推动治理的联动与融合。
三、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组织-空间”逻辑阐释
(一)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组织管理机制的协同联动。面对城乡多元组织协作的复杂性难题,帮扶协作组织利用来自更高层级政府的赋权,能够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促进各主体的利益表达,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政府主体方面,帮扶协作组织能够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制定城乡帮扶协作的政策和规划,明确城乡融合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实现资源调配与整合。同时还能对城乡帮扶协作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工作质量和效果。市场主体方面,帮扶协作组织能够通过原单位的资源力量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引导市场资源下乡,培育农村地区的市场主体,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通过引进企业投资农村地区的产业项目,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社会主体方面,帮扶协作组织能够通过引进社会力量,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社会力量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支持,成为政府和市场力量的重要补充。总之,帮扶协作组织成为多元主体的协调者,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激发多元主体力量,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面对科层组织的多层级性难题,通过在市、县、乡、村各层级建立多层级帮扶协作组织体系,可与当地科层组织层层对应,实现各层级间在沟通、协作和资源上的协同联动。多层级的城乡空间结构塑造了多层级的帮扶协作组织体系,通过强化治理协同,提升帮扶协作组织体系的效能,实现城乡多层级的治理融合。乡域的治理融合需要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如采用党组织共建、帮扶干部挂任当地政府党组织副职等方式,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合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力量,实现对政治和行政资源的统筹,推动城乡融合的政策进程。村域内更是要通过发挥组织成员个人的治理经验优势,为基层组织带来更加成熟的治理理念,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总之,城乡帮扶协作有助于从组织层面优化城乡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提升城乡融合的直观感知,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促进城乡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城乡治理融合。
面对乡村治理转型期的“发展悖论”难题,帮扶协作组织能够通过整合城市资源下乡和完善基层组织制度来推动帮扶协作组织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协同联动,从经济层面和治理层面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破解乡村发展困境。一方面,帮扶协作组织能够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实到村到户,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通过整合筹划资源,解决乡村发展中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短缺问题,以外生促内生,激发乡村的内源性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帮扶协作组织协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通过选优配强村“两委”、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等措施,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如推动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村民协商议事形式等方式,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通过增强帮扶协作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协作,发挥经济要素和治理要素的双重作用,推动解决乡村转型的“发展悖论”。
(二)城乡帮扶协作推动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面对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不畅难题,帮扶协作组织进入县域,成为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实现县域集聚的重要主体,多层面进行城乡融合县域空间生产。一是引导资金向县域集聚。帮扶协作组织可以带动财政资金向县域倾斜,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县域建设。例如,通过争取专项债资金、产业有序转移专项资金等方式,支持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通过推动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加大对乡村产业的信贷支持,推动县域产业发展。二是推动人才要素向县域集聚。帮扶协作组织利用返乡下乡人才扶持政策,发挥社会资源优势,鼓励引导在外能人、技术人才、退休干部到乡村一线服务。通过组织开展乡村人才进城培训,提升当地干部和人才的能力。通过推动城乡人才交流,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提升县域人力资源质量,为县域发展注入活力。三是推动产业向县域集聚。帮扶协作组织深度挖掘县域资源禀赋,培育县域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加强产业平台建设,协助建设县域产业园区,推动产业转移和集聚发展,提升县域产业承载能力。总之,通过对资金、人才、产业等要素的县域集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空间的融合与互动,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面对城乡帮扶协作资源要素单向流动导致的农村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城乡帮扶协作可以通过对县域空间的塑造,提升县域与城市的空间协调。一方面是通过促进县域物质空间的改善,改善农村地区发展短板,增强县域发展韧性。通过协助当地制定城乡一体化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空间,实现城乡发展空间一体化,促进城乡功能互补和协同发展,改变县域的物质空间形态,提高县域空间的生产能力和居民生活质量,夯实县域的发展基础,进而推动城乡互补、城乡互促,实现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县域内精神空间的改造,促进县域与城市的理念对接。通过给县域带来先进的发展和治理理念,激发农村发展思路。帮扶协作组织通过给基层政府带来先进治理理念,可以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拓展发展思路,实现与高层级政府发展理念的对接;通过给企业和农民带来先进发展理念等方式,在县域内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避免产业同质化导致的持续性发展问题。总之,城乡帮扶协作可通过以县域空间为载体以及县域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改善,提升县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面对县域内多层级城乡空间结构内资源要素流动不畅的梗阻,帮扶协作组织可通过建立多层级的组织体系实现各个层级的组织互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村要素的虹吸效应和乡村振兴中城市要素对乡村的扩散效应构成了由城域和乡域组成的城乡空间,包含了县城、乡镇、农村多个空间层级。帮扶协作组织通过构建覆盖各空间层级的帮扶协作体系,推动县域各层级间的要素流动,增加各层级资源的协作与沟通,构建县域内的空间主体关系和秩序。在该体系内,县城是城乡深度融合的载体,乡镇是联城带村的纽带,农村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形成了县乡村融合的县域发展体系。通过帮扶协作组织与当地政府的三级联动,形成县乡村协作的有机整体,实现了包括县乡村三个层面的经济增长和功能完善。通过统筹高层级的发展规划,推动项目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了县域各层级的发展效率,推动了以县域为空间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
(三)“组织-空间”交互作用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逻辑。在此框架下,组织与空间结构呈现出深度融合的互构关系,形成了组织系统对空间要素的重组能力和空间载体对组织运作的赋能作用,共同构建起城乡要素流动的动态网络。组织结构利用治理工具影响空间功能分化,空间结构则反向塑造组织的运作模式。组织层面,帮扶协作组织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建立多层级组织体系以及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协同联动,在纵向层级间构建起资源调配的传导链条,在横向区域间打破行政壁垒形成跨域协作,使城市资源要素通过组织化方式注入县域空间,而乡村特色资源则依托组织网络实现市场化,形成城乡治理融合的组织逻辑。空间层面,空间结构为组织的治理运作提供物质载体与场域,通过城乡资源要素县域集聚、增强县域空间改造、构建县域空间的层级互动体系,凝聚各类组织要素交互作用的载体,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在县域空间中打造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型空间单元,形成城乡治理融合的空间逻辑。
(四)组织与空间的互构,本质上是制度创新与空间重构的双向调适过程。这种调适机制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展现出城乡帮扶协作体系下制度灵活性与空间可塑性协同演进的理论逻辑。空间结构在县域内为帮扶协作提供组织运作的载体,实现帮扶协作多层级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塑造,促进县域内多层级的多元主体协作;组织结构则通过协同治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乡空间的整合与优化,推动城乡空间内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帮扶协作通过塑造组织逻辑和空间逻辑,形成两种逻辑的相互嵌入和双向推动,消除城乡治理融合存在的组织联动隔阂和资源流动梗阻,提高城乡治理的效率和力度,增强城乡治理的协同性和适应性,提升城乡治理融合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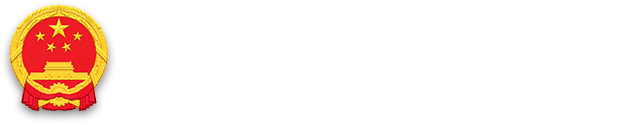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1802000181号
粤公网安备 44011802000181号